国人为什么没有信仰?
国人为什么没有信仰?
资讯来自网络;原创 古影人 形而下的哲思 北京
今天中国的问题,恰恰不在于文化的断裂,而在于文化的固执,它使得坚固的现实在它面前也不得不让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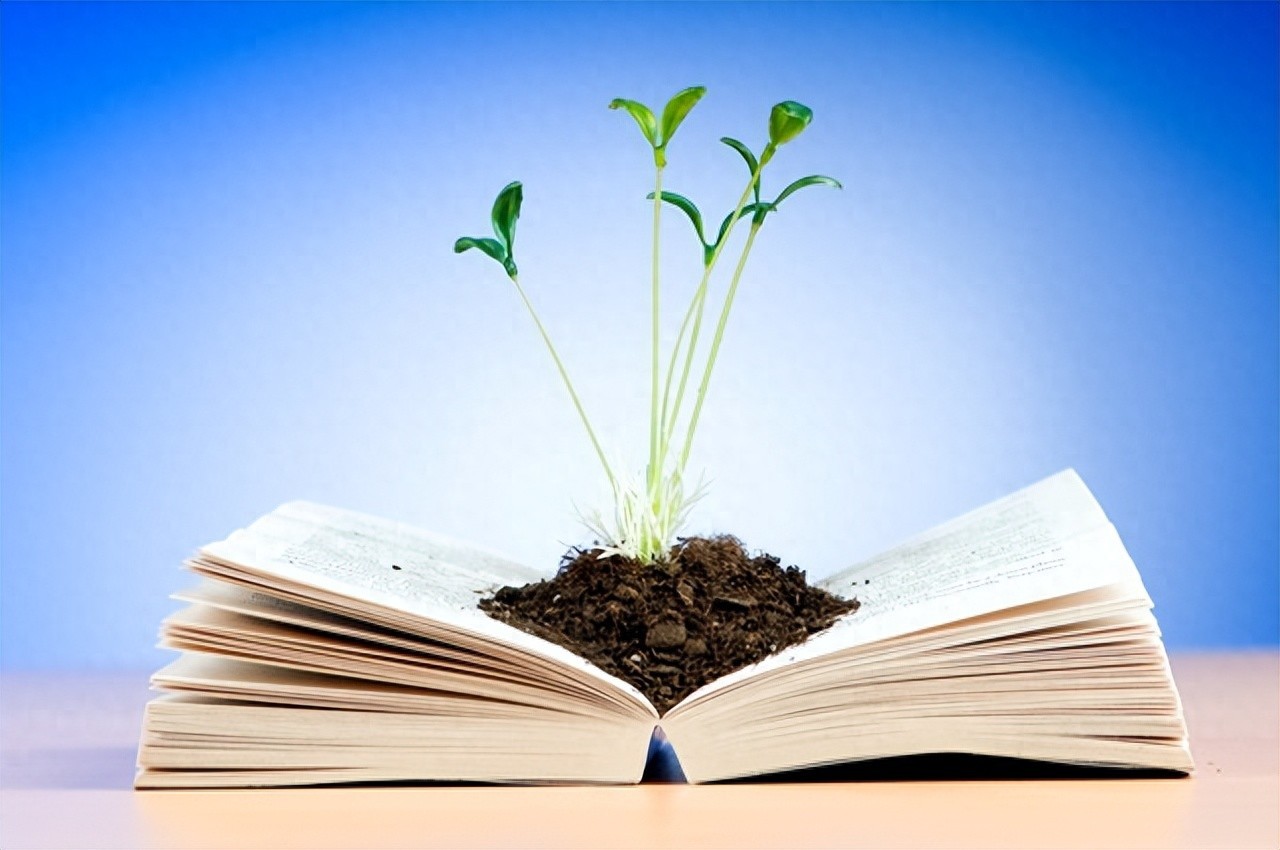
国人为什么没有信仰:一个真问题还是假问题?
01
没有无辜的问题。
国人为什么没有信仰,这是一个被不断问及的问题,然而当人们沿着这个问题所铺设的轨道向前思考的时候,恰恰会陷入由这个问题所设置的陷阱当中。因为在这个问题背后预设了这样一个理所当然的事实,即信仰是一种普遍的现象,而当认为所谓的国人没有信仰时,便出现了与理所当然的事实相反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赋予国人以信仰便成为这一问题在客观上试图完成的目标。
也就是说,答案本身隐藏在问题当中,当人们追问国人为什么没有信仰并且将其视为一个真实而严肃的事实时,问题的答案已经不再重要,重要的是问题本身。换言之,只要当这个问题本身被严肃地对待并且不会质疑它的真假时,答案就已经浮现了,或者问题已经被完成,人们自以为才刚刚开始,实际上已经结束了。
在这里,关键的不是问题的答案,而是为什么会有这个问题。
所以,没有无辜的问题,任何问题的追问方式早就预设了答案,或者说只有答案逐渐清晰的时候,问题才会浮现出来。这意味着,一种真正的思考或者回答问题的方式,不是直接回答问之所问,而是反过来追问问题本身。
关于国人为什么没有信仰这个问题,反过来的问法才能显示出这个问题的关键:为什么西方人有信仰?或者进一步追问为什么会有信仰这种东西?
执着于解释国人为什么没有信仰,或者反过来肯定国人存在信仰(看似对这个问题的否定,实际上仍旧是对它的肯定),都不是对这个问题的真正回答。因为对于国人来说,信仰本来就是一个十分陌生的东西,它不属于中华文明的组成部分,而是西方文化乃至社会的基本结构。
当人们用西方文化的要素反过来叩问中国文化时,这种叩问本身就是一种反向的文化认同,即我们在追问的过程中所认同的不是我们的文化(而我们自以为是在认同我们的文化),而是在无意识中接受了西方文化,将其视为普遍的范式予以接受,然后反过来将我们变成一个例外。
于是在这种追问中潜意识地形成了这样一种中心与边缘的二分,即有信仰的民族或文化处于中心地位,而没有信仰的民族或文化处于边缘,而处于边缘的民族必须以中心为方向。
这就是为什么在这种追问中答案已经隐藏在问题本身当中,这也意味着这不是一个真正的问题,它既非真,也非假,而是一个祈使句,是一种隐藏有特定规范的要求,即要求国人必须解决信仰问题,否则我们的民族就是一个有缺陷的民族(当然,任何民族都有自己的缺陷,但这并不意味任何缺陷都必须通过另一个民族来发现并且以对方为标准,相反,审视民族缺陷与解决的依据始终是一个民族的现实生存状况)。
因此,这个问题背后反映的是一种文化殖民,而且是文化的自我殖民,因为追问这个问题、并且将其视为一个严肃话题的不是西方人,而是我们自己,因为我们早已将信仰接收为一种理所当然的事实,但这样的事实在事实上从未构成我们民族文化的一部分。由这一问题所引发的文化反思也并不是真正的文化反思。
在这种情况下,正如上文所说,无论回答国人有信仰还是没有信仰,都不是对这个问题的真正回答,追问国人是否有信仰或者为什么没有信仰,本来就是一个范畴错误。

02
那么,这是否意味着我们将无法讨论信仰问题?是否也意味着我们无法真正开展文化评价与反思?
显然不是。一种真正的思考不是在接受某些亘古不变或者理所当然的事实的前提下寻找它的反常,而是拒绝承认一切理所当然的东西,通过思维清零或者思维的陌生化方式发现真正的问题。这样的问题虽然也不是无辜的,但至少不存在明显的预设与倾向,因而是一种自由的思考。
在信仰问题上的思维清零就是拒绝承认信仰是一种理所当然的民族现象或者文化现象,即不是将其视为一种自然现象或普遍现象,而是认为它本身就是一种源自于地方性的特殊现象。在这种情况下,应当追问的不是国人为什么没有信仰,而是追问为什么西方人有信仰?
当然,准确来说追问西方人为什么有信仰本身也是一个虚假问题,因为它同样是站在国人的立场上反过来审视西方文化,因而是一种因为文化的偏差而导致的问题。
在西方文化内部,信仰也是一个陌生的概念。这不是说西方文化中没有信仰,而是说西方人并不会用信仰这个概念审视自己的文化或者宗教,信仰只是在文化交融的过程中产生的。
当西方人第一次看到有其他民族竟然不需要有一个至高无上的神依然可以产生秩序、延续历史的时候,信仰的观念才第一次产生,即第一次认识到他们的宗教就是他们的信仰,而其他民族有可能没有信仰。反过来,当中国人第一次认识到一个民族的社会生活以宗教为核心的时候,他也开始认识到原来还有信仰这种东西。
文化的交融对于不同民族的文化来说既是认识自己也是认识它者的镜子,信仰就是其中的一面。在这里,信仰也只是扮演着认识的功能,但在“国人为什么没有信仰”这一问题中,信仰不再仅仅是一面镜子,而是一把尺子,它扮演的是文化的规范与约束的功能,其潜台词是说,应当用这把尺子去规范我们的文化。但这把尺子本身是否恰当,并没有人思考过这个问题。
从深层次来讲,在文化的领域没有什么是理所当然的。这既体现在对其他文化的认识上,更重要的是,它也体现在对自身文化的认识上。将其他民族的文化视为理所当然的,就是用其他文化否定自身的文化,这是一种文化的自我殖民;将自身的文化视为理所当然的,就是用自身的文化否定其他文化,是拒绝对自身的文化进行反思,这是一种文化保守主义乃至原教旨主义。

03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在信仰的背后不存在普遍性的东西。信仰的核心是价值,外围是宗教或者其他类似宗教的形式。每个民族都有自身的价值,但并不意味着每个民族都有信仰,因为价值并不必然表现为信仰。
在以信仰为价值的文化中,价值出现在民族生活之上,也就是彼岸世界,在这种价值体系中,此岸世界与彼岸世界保持着一种紧张关系,二者相互否定,选择彼岸世界就无法选择此岸世界,反之亦然,这就是为什么各种宗教的共同特征就是存在一个超越于世俗生活的神,它是彼岸世界的象征。而在中国,不存在彼岸世界与此岸世界的二分,此岸的世俗世界就是一切,因此其价值不在于遥远的彼岸,而在活生生的此岸。
这是东西方价值的不同,而不同的价值会带来不同的生活方式,或者准确来说是不同的生活方式决定了不同的价值,价值的形式则具有多样性,有信仰形式的,也有非信仰形式的。
在今天,西方文化也迎来了世俗时代,“上帝已死”意味着西方宗教世界的崩塌。但如果就此认为西方文化完成了对自身的决裂,这就是一种误解。西方虽然迎来了世俗时代,但这也只是信仰在宗教形式方面的变化,其价值的内核仍旧十分坚固——要知道西方价值的对象或者归宿并不一定是上帝,而是由上帝所体现的此岸世界与彼岸世界的对立,不过这种对立也只是一种表象,在背后是西方人对人本身的不信任,这使得西方人始终试图在人之外寻找价值的根源,在宗教时代它是上帝、是彼岸世界,在今天则转化为对超越于人的理性、科学的信仰,在这一点上西方文化是一脉相承的。
同样,今天的中国文化虽然与传统文化存在巨大的裂痕,但实际上今天的中国人从未离开传统半步。在中国文化中,最高的价值就是人,没有比人更高的价值,所以对于中国文化来说,人与人的关系是最重要的关系(在西方是人与自我的关系)。
这一核心价值在今天有过之而无不及,关系、人情在今天的中国仍旧是最重要的社会资源。弘扬传统文化成为今天的主流,但实际上传统并不需要弘扬,它就在那里,断裂的不是作为传统文化内核的价值,而是礼仪等形式,但后者在文化中只是外围不是内核。
或许今天的国人真正需要思考的不是文化的传承问题,而是文化的变革问题——传统文化的护城河太坚固以至于它反过来成为现实的原因而不是结果,换言之,今天中国的问题,恰恰不在于文化的断裂,而在于文化的固执,它使得坚固的现实在它面前也不得不让步。
这可以解释在全球化的今天,为什么东西方并没有因相互交往而变得趋同,反而变得更加剑拔弩张——双方都没有变化,变化的只是双方以更加切近的方式遭遇,在这种情况下,冲突是必然的。

资讯
-

- 顺治帝只活了24岁,一生独宠董鄂妃,为何能生下17个孩子?
-
2025-07-15 16:03:58
-

- 生肖猪在龙年要注意什么呢
-
2025-07-14 15:26:41
-

- 企业降本增效有哪些方法和措施?
-
2025-07-14 15:24:25
-

- 盘点那些让你一眼难忘的手机代言人,他们谁是你心中的NO.1
-
2025-07-14 15:22:09
-

- 高性价比手机推荐,这三款有旗舰配置价格还便宜,堪称性价比之王
-
2025-07-14 15:19:53
-

- 鱼柳不煎、不炸、不蒸,做法简单又好吃
-
2025-07-14 15:17:37
-

- 消防主题儿童画|消防员创意画|安全主题画,一起来学习画画吧
-
2025-07-14 15:15:21
-

- 任鲁豫,央视舞台上的多元主持华章
-
2025-07-14 15:13:05
-
- 教你做鲜美多汁的肉馅白菜卷,一口咬下去别提有多美味!
-
2025-07-14 15:10:49
-

- 不一定要逆风翻盘,但一定要向阳而生
-
2025-07-14 15:08:33
-

- 我国的省份,你了解多少?
-
2025-07-14 15:06:17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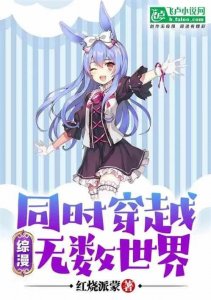
- 此生必看的综漫小说,全是精品
-
2025-07-13 23:53:09
-

- 楚月《寻侠英雄传》央六热播 《芈月传》“香儿”再战侠女
-
2025-07-13 23:50:52
-

- 文史 | 郭解,惊动汉武帝的“黑老大”
-
2025-07-13 23:48:37
-

- 世界5大神秘家族,被称操控世界的幕后推手,中国两大家族占首榜
-
2025-07-13 23:46:20
-
- 申请专利:益处概览
-
2025-07-13 23:44:04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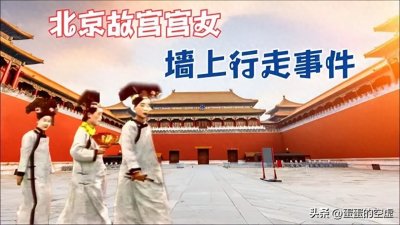
- 故宫灵异事件
-
2025-07-13 23:41:48
-

- 派大星和海绵宝宝的日常友谊语录
-
2025-07-13 23:39:32
-

- 今年“看一集停不住”的4部剧,部部口碑爆棚,错过一部可惜了
-
2025-07-13 23:37:17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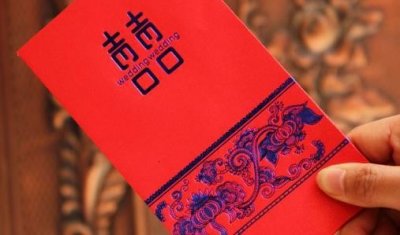
- 结婚红包吉利数字一览表
-
2025-07-13 23:35:0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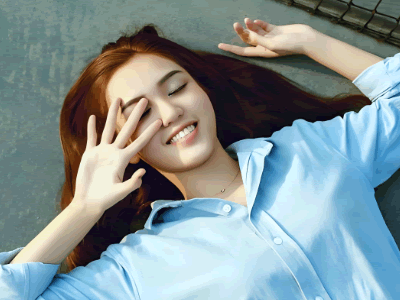 宝藏女孩——陈钰琪全图写真合集
宝藏女孩——陈钰琪全图写真合集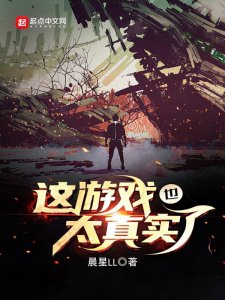 推荐九本模拟经营小说,经营领地和商铺(二)
推荐九本模拟经营小说,经营领地和商铺(二)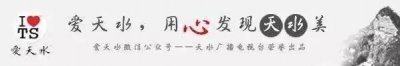 号外|“天水南站—麦积山温泉”专线公交开通啦!高铁+温泉说走就走!
号外|“天水南站—麦积山温泉”专线公交开通啦!高铁+温泉说走就走! 圣女贞德:美貌绝伦,率军抗击侵略者,落入敌手惨遭凌辱受刑而亡
圣女贞德:美貌绝伦,率军抗击侵略者,落入敌手惨遭凌辱受刑而亡 QQ飞车手游:没有好看的相册?手把手教你制作精美的三格图
QQ飞车手游:没有好看的相册?手把手教你制作精美的三格图 北部湾包括我国哪些城市,发展前景如何?
北部湾包括我国哪些城市,发展前景如何? 排超第一美女:与龚翔宇同队同乡且自幼相识,王辰玥如今大不同
排超第一美女:与龚翔宇同队同乡且自幼相识,王辰玥如今大不同 武警部队级别解析:正大军区级的独立军种
武警部队级别解析:正大军区级的独立军种 英雄联盟:仙灵女巫(璐璐)全方位解析……你喜欢这个英雄吗?
英雄联盟:仙灵女巫(璐璐)全方位解析……你喜欢这个英雄吗?